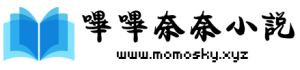第25章 镇南侯府的千金还精通医术?
钟毓灵睫毛动了动,不再言语,车厢内再度恢复了安静。\b!i·q¢i¨zw¨w?.c^o!m¨
回到国公府,钟毓灵径直回了自己的院子。
热水很快备好,巨大的楠木浴桶里撒满了安神的花瓣,雾气氤氲。
春桃心疼地看着她手腕上的青紫,想要上前伺候。
“主子,让奴婢帮您吧。”
钟毓灵却摇头:“我喜欢自己洗澡。”
“可是……”
“我要自己洗!”钟毓灵坚持。
春桃知道跟她说不清楚,只能道:“是,那奴婢就在外面候着,您有事就喊一声。”
房门被轻轻合上。
钟毓灵走到浴桶边,褪下层层衣物。
当最后一层中衣滑落,她白皙纤细的手臂上,缠绕着的东西终于显露出来。
悬脉丝细若蝉翼,在水汽的映照下泛着几不可见的银光。
她解开丝线的活扣,一圈,又一圈。
钟毓灵将那团丝线放在一旁,缓缓沉入温热的水中。
今天在崖边,是一场豪赌。
她赌沈励行就是那个试探她的人。
赌他会出手。
先不说她嫁入国公府就死了,对皇上对侯府都不好交代,哪怕是为了国公夫人的心疾,也不会放任她去死。
所幸,她赌赢了。
但钟毓灵从不将自己的性命,完全寄托在一个男人的心血来潮上。
她抬起手,看着隐隐被勒出红痕的手臂,手指缓缓握紧。
若是沈励行没有出现,或是选择袖手旁观,在她被翠玉推下的那一瞬间,这悬脉丝便会缠上崖边的树根。
她死不了。
当然,她也不介意顺手将那个对钟宝珠忠心耿耿的翠玉,也一并拖入深渊。
温热的水流漫过肩头,将她整个人吞没。
钟毓灵闭上眼,缓缓向着桶底沉去。
水流堵住了口鼻,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响。
窒息的感觉从胸腔开始蔓延,带着灼人的痛意,一寸寸攫取着她的神志。!l^a/o′k.a.n·s/hu+.`c+o!m_
就是这种感觉。
与她在镇南侯府,被宋氏按在水缸里“学规矩”时一模一样。
那种无法呼吸,拼命挣扎却只能换来更粗暴对待的绝望。
那种身为蝼蚁,任人践踏的羞辱。
只有这种濒死的体验,才能时时刻刻提醒她,那些刻骨铭心的恨意。
提醒她,她是如何从地狱爬回来的。
她要复仇。
她要将那些人曾经施加在她身上的痛苦,百倍千倍地奉还!
在意识消散的前一刻,钟毓灵猛地挣扎着从水中探出头,发出一阵剧烈的呛咳。
水珠顺着她湿透的青丝滑落,淌过苍白却再无半分怯懦的脸庞。
她大口地呼吸着,胸膛剧烈起伏。
雾气氤氲中,那双曾经天真无邪的杏眸,此刻只余下一片深不见底的寒潭。
……
一晃数日。
国公夫人的病,竟真的肉眼可见地好了起来。
从前只能终日卧床,如今脸色红润了许多,偶尔还能在嬷嬷的搀扶下,去花园里走上几步,晒晒日头。
府里的下人们都说,这新来的世子妃,看着不声不响,倒还真有几分神鬼莫测的本事。
这一日,钟毓灵照常提着针盒来到国公夫人的正房。
还未进门,便听见里面传来一阵许久未闻的笑语声。
“姐姐,你没事就好,我这一路快马加鞭赶回来,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一道急切的女声传来。
钟毓灵脚步一顿。
屋内,国公夫人靠在软枕上,难得地露出一丝笑意。
“清沅,你这性子,还是这么风风火火的。”
国公夫人无奈道:“放心吧,我这一时半刻还死不了。”
安远侯夫人苏清沅握住她的手,上下打量着,啧啧称奇。
“何止是死不了,我看你这精神头,比去年见时还好些。xi,n_x¨s¨c+m,s^.¢c\o′m\都说你这心疾是沉疴,连宫里的太医都束手无策,怎的……”
苏清沅的话还未问完,钟毓灵就提着针盒直接闯进来了。
她刚过来,就看见了陌生的苏清沅,脚步一停,露出了疑惑的神色:“新姨姨?”
苏清沅更是纳闷:“姐姐,这是谁,怎么这般没规矩,连个通传都没有就直接闯进来了?”
国公夫人脸上的笑意淡了三分。
她朝着钟毓灵的方向略抬了抬下巴,语气平平。
“我儿慎行新过门的媳妇,钟氏。”
“哦”苏清沅恍然大悟,拉长了语调,“原来她就是镇南侯府的那位千金啊。”
她的目光在钟毓灵身上扫了一圈,从那张懵懂的小脸,到身上还在守节期穿的素色衣裙。
“我听闻,镇南侯的千金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京中有名的才女,怎么今日一见,瞧着……”
她的话没说完,但意思再明显不过。
怎么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
国公夫人显然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谈,只淡淡道:“此事说来话长。”
她转而看向钟毓灵:“过来,施针吧。”
“哦,好!”
钟毓灵反应过来,走过来一下坐在了床边,直接把苏清沅给挤下去了。
苏清沅被这么一挤,脚下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在地。
她站直身子,刚要转身发怒,钟毓灵已经自顾自地打开了针盒,从里面捻出一根细长的银针。
她捏着针的手高高举起,那模样,怎么看怎么不靠谱。
苏清沅心头猛地一跳,脱口而出:“等下”
话音未落,钟毓灵的手腕忽然一落。
那根银针便如一道倏忽而逝的流光,快准稳地刺入了穴位。
苏清沅的呼吸停了一瞬。
紧接着,是第二根,第三根……
钟毓灵的动作依旧看着有些笨拙,可每一针落下,都精准得令人心惊。
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国公夫人的身上就已落满了银针。
苏清沅剩下的话,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全都卡在了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很快,钟毓灵便收了针,又恢复了那副乖巧懵懂的模样,低头认真地收拾着针盒,仿佛刚刚那个出手利落的人,根本不是她。
“姐姐,这……”
苏清沅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她快步走到床边,难以置信地看着国公夫人:“你真让她给你扎针了?”
国公夫人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原本苍白的脸上竟多了几分血色。
她靠着软枕,语气淡淡:“她人虽然瞧着愚笨,但这手针灸的功夫,怕是宫里最好的御医也比不上。”
苏清沅的瞳孔骤然一缩,一个念头闪电般划过脑海。
“所以你身体有所好转,竟是因为她?”
她的目光落在那个正低头整理银针的钟毓灵身上,充满了审视与不解。
“可我怎么从未听说,镇南侯府的千金还精通医术?”
心中的疑云越来越重,苏清沅鬼使神差地凑近了些,想从那张天真无邪的脸上瞧出些什么端倪。
她刚一靠近,钟毓灵就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兔子,猛地抬起头,一双清澈的眸子睁得溜圆。
“呀!”
她慌不择路地猛然站起,脑袋不偏不倚,眼看就要撞上苏清沅探过来的下巴。
苏清沅惊得倒抽一口凉气,急忙后仰。
钟毓灵却比她反应还大,脸上瞬间布满了孩童般的惊慌与担忧,她踮起脚尖,撅着嘴就要凑过来。
“姨姨对不起!灵灵给姨姨呼呼!”
她的小嘴鼓成了个包子样,作势要吹气。
“呼呼就不痛了!”
那张傻乎乎的脸蛋在眼前放大,苏清沅吓得连连后退,伸手将她拦住。
“别!你别过来!我没事!”
钟毓灵一下站定了,茫然不解的看着慌张的苏清沅。
苏清沅惊魂未定地站直,盯着钟毓灵,好一会才开口:“姐姐,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国公夫人望着苏清沅懵懂的脸,疲惫地叹了口气。
“清沅,你先坐。”
她的声音里透着一股无奈。
苏清沅是她从小到大的手帕交,这些糟心事,没什么好瞒的。
于是,国公夫人便将镇南侯府如何偷梁换柱的始末,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随着她的讲述,苏清沅的脸色由惊转怒,最后变得铁青。
“啪!”
她一掌拍在床沿的矮几上,茶杯都跟着跳了一下。
“镇南侯府欺人太甚!”
苏清沅的声音里满是怒火,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他们怎么敢!竟送了这么一个傻子过来羞辱你!羞辱国公府!”
国公夫人摇了摇头,眼底掠过一丝精明与冷意。
“话不能这么说。”
“当初两家定下的婚书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是镇南侯府嫡女。”
“钟毓灵,她也是嫡女。”
“我们只能认下这个哑巴亏。”
苏清沅气得站了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
“不行!这口气我咽不下!”
她猛地停住脚步,转身看着国公夫人,眼神决绝。
“姐姐你别管,我这就去镇南侯府,替你讨个说法!”
“站住!”
国公夫人出声喝止了她。
苏清沅的脚步顿住,不解地回头。
“你去了,打算如何?”国公夫人的语气平静得可怕。
苏清沅想也不想地答道:“自然是让他们把钟宝珠换回来,履行婚约!”
国公夫人闻言,竟轻轻笑了一声,只是那笑意未达眼底。
“换回来?”
“清沅,你当真以为,那个钟宝珠是什么好相与的?”
“一个为了逃避婚约,不惜将亲姐姐推出去顶替的女子,你觉得她会安分守己地嫁过来守寡?”
国公夫人扶着床沿,缓缓坐直了身体,目光落在不远处那个正低头摆弄针盒的钟毓灵身上。
“与其迎一尊工于心计的菩萨进门,整日里想着怎么作妖,我还不如留着这个。”
“至少,她还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