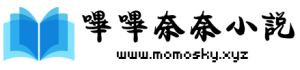第67章 门没开,可风先到了
第67章门没开,可风先到了
北境的雪还没化尽,山脊上一道新凿的暗道蜿蜒如蛇,藏在残冰碎雪之下。^8′1k!s.w?.^c!o?m¢
春风贴着地皮溜进来,带着马蹄踏雪的闷响,也带起了太庙东厢那袋供奉粮食扬起的微尘。
京中已有三日不得安宁。
“代州立碑了谢氏碑!边民跪拜,香火不断!”
“你还不知道?昭宁长公主早就在北境插旗,百姓只认她的令,不听朝廷诏!”
“我表兄的舅丈亲眼所见,夜里山头有光,写着‘菜儿承统’四个字,风吹过就亮……”
茶肆酒坊里,这些话像野火燎原,从贩夫走卒口中滚出,一路烧进宫墙。
连御前洒扫的小黄门都听见老太监嘀咕:“怕是要变天。”
而这一切的源头,此刻正坐在一间不起眼的山间驿馆内。
谢梦菜低头翻着一本《农政辑要》,指尖却停在“春垦宜早”四字上,久久未动。
她穿素色锦袍,外罩狐白披风,发髻用一支银簪松松挽住,看上去不过是个随行文书的女官。
但柳五郎知道,她每根神经都在听着风听那些被风卷起来的言语,如何一步步渗入人心。
“第三批流民已在第七哨安营。”柳五郎低声禀报,手中账本密密麻麻记着粮草出入人丁编册,“韩九娘亲率五百妇孺开荒,今晨已播下第一批粟种。她说,请公主放心,‘刀耕火种,亦能成城’。”
谢梦菜轻轻颔首,目光落在窗外渐次升起的炊烟上。
那是希望,也是棋局的落子声。
“流言散得如何?”她问,声音轻得像在问天气。
“七日内,十二处驼帮经停驿站,共植入三十七条口信。¥o5£_¨4+看?书?`2更 谢梦菜终于抬眸,眼底映着远山初绿,笑意却冷:“他们越慌,就越会自己挖坑跳。” 话音未落,门外脚步沉稳,黑影投地。 程临序推门而入,甲胄未解,肩头还凝着霜粒。 他将一卷油布地图放在案上,双手奉上,动作规矩得近乎生疏仿佛仍记得那纸婚契上的“互不相干”。 “七条隐道贯通八城。”他嗓音低哑,像砂石碾过铁板,“轻车三月可行,重辎夏末可运。北境再不是死地。” 她展开地图,指尖缓缓划过那些曲折线路,忽然问:“你可知为何我选在雪未落时动手?” 他一怔。 “因为真正的路,要赶在绝境之前打开。”她抬眼看他,目光如雪后初阳,灼得他心头一颤,“就像那年,你翻墙进我院子也是在婚契生效前。” 风骤起,吹动窗棂,卷起她鬓边一缕碎发,也掀起他披风一角。 两人之间,雪末轻扬,似有千言万语,终归沉默。 可这沉默,比任何誓言都重。 与此同时,京城崔府深处,烛火摇曳。 宗正寺卿崔元柏手握茶盏,指节发白。 堂下坐满旧党重臣,人人面色凝重。 “民心若失,祖制难继!”一人拍案而起,“如今街头巷尾皆传‘谢氏碑’‘昭宁旗’,竟还有人说夜见天书降世,写的是‘菜儿承统’!这是谋逆!是妖言惑众!” 话音未落,忽闻窗外风急,檐下铜铃“叮当”作响。0$??0小§说¤:网eˉt已t£`发£]布?最¤新?章3<节?. 那声音起初寻常,可片刻后竟似有了节奏,细听之下,竟如人语残音 “菜……儿……承……统……” 满堂死寂。 众人悚然回顾,唯见香炉中识心灰轻扬,烛火剧烈晃动,映得墙上人影如鬼舞。 “是风……是风动铃……”有人颤抖开口。 可谁都知道,这不是风。 那是从地脉深处爬上来的讯号,是无形之网收拢的第一声震颤。 而在城南一处僻静小院,沈知白正提审一名佝偻老吏。 那人曾是伪诏案中的誊抄小吏,畏罪潜逃多年,如今被秘密带回,却不料朝廷非但未加刑罚,反赐汤药温言安抚。 他泪流满面,终于吐露真相:“当年改诏那夜……主谋压纸用了一枚玉镇纸,印出暗纹……形如‘山断雪裂’……我记得清清楚楚……” 谢梦菜坐在内室屏风后,听着一字一句,瞳孔微缩。 她当即命人取过程临序历年军报存档,在数十份奏折末角细细比对果然,每一纸“通路已开”的捷报,都盖着同样的暗印:山势断裂,积雪崩裂,正是“破障前行”之意。 她盯着那枚印痕,久久不语。 良久,她起身,走到门前,望着天边一抹将明未明的晨光。 然后,她轻轻道:“放了他。” 沈知白一惊:“公主,此人知晓内情,岂能轻易释放?” “留着他,才是杀招。”她转身,唇角浮起一丝极淡的笑,“把他安置在崔府附近,赁屋而居。让他……好好说话。” 她不动声色。 那佝偻老吏跪在堂下,涕泪横流,供完最后一句“玉镇纸压诏书”,便伏地颤抖,等着枷锁加身牢狱吞噬。 沈知白眉头紧锁,掌心已沁出冷汗这人是伪诏案唯一的活口,一旦泄露出去,旧党必将倾巢反扑;可若留着,又是颗随时会炸的火雷。 “放了他。”谢梦菜的声音从屏风后传来,轻得像一片雪落屋檐。 沈知白猛地抬头:“公主?” 她走了出来,素衣未改,眸光却如刃出鞘。 她看着那老吏,语气平缓:“赐银五两,赁屋安居,邻里皆知他曾为太常誊录旧档。” 众人愕然。 唯有柳五郎眼底微闪,立刻会意。 三日后,崔府西角巷口多了一间矮屋。 屋主是个病嗓老头,每日清晨扫阶晒药对街坊絮叨往昔宫中秘事。 起初无人在意,可渐渐地,茶摊酒肆竟都传开了 “听了吗?那年改诏,用的是‘山断雪裂’玉印!” “不止!我还听说,边关每报捷,就有密信入京,程大将军早就在六部埋了眼线!” “嘘小声些!你没见礼部李侍郎昨儿突然告病?怕是心里有鬼!” 风,越吹越邪。 崔元柏在府中连摔三盏茶,夜半召心腹密议,声音压得极低:“……誊抄吏怎会无罪释放?定是谢氏设局诱我们动手!她要的就是我们自乱阵脚!” “可若真有党册外泄……”一人颤声,“不如……毁了它?” 烛火摇曳,满堂沉默。 当夜,崔府后园偏房燃起幽火。 黑影匆匆将一箱泛黄名册投入炉中,纸灰翻飞如蝶,火光照亮墙角刻着的“宗正旧档”木匾。 火舌舔上“腊月廿三,集议夺玺”几字时,恰好被窗外一双眼睛看得真切。 陆明远带着兵部巡查卫队,打着“查冬防巡火患”的旗号,一路慢行至崔府外街。 他仰头望见那冲天一瞬的红光,唇角微扬,低声下令:“记档崔府亥时三刻私焚文书,形迹可疑,录为备参。” 火灭了,灰散了,可有些东西,烧不净。 三日后,天镜阁。 百官齐聚,仰观星象。 裴砚之立于铜仪之前,长袍猎猎,推演卦辞:“风自北来,携雪气入城,扰庙铃动香灰乱人心非天示警,乃人借势。” 群臣哗然。 谢梦菜静立高栏之侧,披风轻扬,目光掠过一张张惊疑不定的脸。 她忽而启唇,声不高,却落如重锤: “若一道风能吹倒七座门,那开门的,是风,还是门自己松了榫?” 话音落处,死寂如渊。 就在这刹那,李长风自阁外疾步而入,甲胄铿然,双手呈上一方锦盒。 盒中,是几片焦黑残页边缘卷曲,墨迹模糊,唯有一角清晰可辨: “腊月廿三,集议夺玺”。 满殿倒吸冷气。 崔元柏面如死灰,踉跄后退半步,撞翻身侧青铜鹤灯。 而阶下,程临序负手而立,铁甲映着天光,目光冷峻如霜。 他没有看那残页,也没有看崔元柏,只是微微侧首,望向栏上的女子。 那一夜,他的弓弦曾为她震断灯芯,只为不让她在黑暗中独坐。 如今,她已不必躲藏。 风已过境,门将倾塌。 而更烈的旱,正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