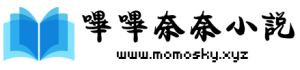二〇八、至亲反目(十四)
林蕈脸上写满了困惑,不解地望向我。·5′2\0?k_sw?._c!o.m^
我沉声剖析:“他今天来看我,对你刚才说的那番话只字不提,这恰恰说明他心知肚明凭他自己,根本说不动我去坐那个狗屁行长的虚位。但他算准了,只有你能说动我。”
“宏军,”林蕈急切道,“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你没必要真遂了他的意!”
我嘴角的苦涩更深:“你还是没看透。你以为不真金白银投进去就没风险?错了!他若真敢利用银行窃取国资,你和达迅照样会被拖入深渊,万劫不复!他早算准了你会来劝我,也算准了我为了护你周全,明知是坑也得跳!只有我坐在那个位子上,才能最大限度替你挡下风险,把火烧到我这边。”
林蕈更加困惑,眉头紧锁:“这……这不是悖论吗?你为了保全我,岂不是首接挡了他的路?他怎么会容忍?”
“这正是他高明又狠毒的地方!”我声音冷了下来,“他不会只靠一招。他懂得利用一切缝隙一切软肋迫人就范。今天他捏住了志明这张牌,逼你就范,进而逼我。明天呢?他手里难道就没有别的牌,没有别的软肋可捏吗?眼下,他只需先把我们这些‘卒子’拱过河,摆到棋盘上他想要的位置。至于后面怎么驱使我们怎么落子怎么将军……他的后手,如影随形。”
林蕈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栗:“他这个人……太可怕了。”
“表面看,是这场天灾给了他可乘之机。”我眼神犀利,仿佛穿透了表象,“但更深层,是他洞穿了人性的弱点,把我们一个个都当成了他‘鹬蚌相争’里的角色,自己稳坐钓鱼台,等着当那个得利的渔翁。”我略作停顿,声音里带着一份幸灾乐祸,“说起来,这次,我们还不是最惨的那个。”
“谁更倒霉?”林蕈追问。
“他假惺惺来看我,嘴上说是要替我‘出气’,要对田镇宇郑桐他们下手,”我冷笑一声,“实则是想借着这股‘义愤’,对他们敲骨吸髓!用不了多久,他们辛苦积攒的财富,就得改姓岳了。”
林蕈倒吸一口凉气,脸上血色褪尽:“原来……在他眼里,我们都是被他玩弄于股掌的傻瓜。”
我嘴角勾起一抹难以捉摸的弧度,带着不以为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岳明远再算无遗策,终究也是个人。是人,就有软肋。”我的目光变得深邃,“他费尽心机要把我推上那个正处级行长的位置……你说,我是不是该好好‘感谢’他?毕竟,多少人挖空心思削尖脑袋,也够不着这样的‘机会’呢。x?h·u/l_ia\n,.+c/o′m_”
林蕈脸上忧色更浓:“宏军,别逞强,万一……”
“怎么,怕我斗不过他?”我故意扬起声调,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林蕈,我可是出了名的打不死!老天爷都拿我没辙,他岳明远又能拿我怎样?我非得让他这次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
女人的敏锐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林蕈竟在这种关头捕捉到了奇怪的重点,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酸意追问:“赔了夫人?你指哪个夫人?是那对双胞胎里的姐姐……还是妹妹?”她忽然像是想通了什么,眼睛微微睁大,“难道……两个都让你给……”
“打住!胡说什么呢!”我赶紧截住她的话头,又好气又好笑,“就是个比喻!你这对号入座的本事也太强了吧?”
林蕈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冷气:“关宏军,你那点花花肠子我还看不透?那对姐妹看你的时候,眼神都快拉出蜜丝儿了,你真当我是瞎的?”
我心头猛地一跳。真有她说的那么明显?我怎么……一点都没察觉?难道真是当局者迷?
就在此时,护士进来查房,见我和林蕈还在低声交谈,立刻提醒道:“病人需要休息了,探视改天吧。”
林蕈随即起身:“时间不早,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护士见目的达到,转身离开了病房。
我忙对林蕈说:“这么晚开夜车回去我不放心,不如你就在这儿将就一晚吧?”
“路程也不算远,我自己没问题。”她顿了顿,“再说,我要是留下,有人心里怕要不舒服了。”
“你呀,就是想太多。小敏有陪护床,你去里面套间睡就行。”
林蕈轻蔑地哼了一声:“我可不想当电灯泡。只是提醒你,伤筋动骨一百天,别心急火燎的,落下什么毛病。”
她的话噎得我无言以对,只能眼睁睁看着她走出病房。
她刚离开,彭晓敏便带着几分得色走了进来。
我像审视嫌疑人般紧盯着她,那目光让她不自在地避开了我的视线。
“是你搞的鬼吧?”我首接发问。
她故作无辜状:“说什么呢?听不懂。”
我叹了口气:“你也学坏了。自己不敢赶林蕈走,就让护士出面,这不是借刀杀人么?”
她不打自招,竟没有辩解:“关宏军,你可别好心当成驴肝肺,我不也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吗?”
说完便嘟起嘴,和我打起了冷战。q+s\b!r,e¢a¨d,.¢c/o+m·首到关灯睡觉,也没再跟我说一句话。
黑暗中,薄纱滤过的月光一层层洒进病房,营造出似梦似幻的静谧空间。我躺在病床上,思绪纷乱,毫无睡意。
林蕈的话在脑海中反复回响,一种莫名的恐惧悄然滋生。是啊,当着她的面,我可以夸口不惧岳明远的阴谋诡计,但真正面对他布下的重重机关,却感到力不从心,疲于应付。
我开始剖析岳明远的布局,试图厘清每个人扮演的角色。
首先是陆玉婷。在我生死一线之际,她选择返回省城“求援”。如今看来,这个口蜜腹剑的女人,分明是回去向主子汇报,请示下一步行动。只有她对我与田镇宇等人的矛盾了如指掌,为岳明远“扮猪吃虎”提供了详尽情报。
其次是胡海洋。岳明远动用资源,越级提拔他当上市长,是出于何种目的?我隐约觉得极有可能。当年徐光明的儿子任行长时违背岳明远旨意,结果父子双双被连根拔起。如今安排胡海洋上位,恐怕仍是觊觎这家银行。至于让我当行长,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我无从判断。
那么,彭晓惠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每次与她相见时,她的真情流露……难道都是伪装?她的演技竟比陆玉婷更胜一筹,不着痕迹吗?
彭晓敏呢?她会不会是那个如影随形的密探,将我的一言一行悉数汇报给……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打了个冷战,脊背阵阵发凉。
就在这时,寂静的房间里响起一阵窸窣声。我用眼角余光瞥见彭晓敏缓缓从陪护床上坐起,悄然下地。
我心头一紧,屏住了呼吸。
她果然不是去卫生间,而是轻手轻脚向我这边走来。
我迅速闭紧双眼,心脏狂跳不止。
我的汗毛倒竖,仿佛无数细小的触角在黑暗中伸展,敏锐地捕捉着她的靠近……一步,又一步……我甚至能“感知”到她目露凶光,咬牙切齿,一双手正缓缓伸向我的脖颈,即将扼住……
我猛地睁开双眼,黑暗中,瞳孔骤然迸射出锐利的光芒!
“啊!”她吓得惊叫一声,慌忙捂住胸口,“吓死我了!你怎么了?睡得好好的,突然睁眼……做噩梦了?”
我冷冷质问她:“你过来做什么?”
“我怕你着凉,过来给你掖掖被子。”
我是不是有些草木皆兵太过敏感了?我暗自舒了口气,掩饰道:“刚才被梦魇着了。吓到你了吧?”
她嘤咛一声,竟顺势爬上了我的床,口中还念叨着:“本来躺在那边就害怕得睡不着,让你这么一吓,魂儿都快没了。”
我只好挪了挪身子,给她腾出空间。她像一尾滑溜的鱼钻进被窝,纤长的腿很自然地搭在我腿上,手臂也环住了我的腰。
我提醒道:“疯丫头,这要有人进来,还不得以为咱俩图谋不轨?”
她在我耳边咯咯轻笑:“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又没做什么,心虚什么?再说,门我早反锁了。”
对她这耍赖举动,我只能听之任之,心底却悄然漫上一丝怜惜。
她仿佛陷入回忆,语调带着几分朦胧,像覆上了一缕轻纱:“小时候在福利院,夜里害怕了,我就偷偷溜到姐姐床上。只有挨着她,才能感觉到暖融融的安全感。”
一对无依无靠相依为命的姐妹,在福利院单调而漫长的环境中长大,那份深入骨髓的不安感,我感同身受。想到这里,我轻声问她:“你觉得你姐姐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对我这突然的问题有些不解:“怎么想起问这个?”
“只是有些好奇。”
她思索片刻:“怎么说呢……有时候,她是我在这世上最亲近的人,甚至像妈妈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照顾我。没有她,我可能早就撑不下去了。”
一个失去母爱的人,将姐姐视为母亲,这份情感我自然能够理解。
然而,她话锋一转:“可有时候,她对我的管束比亲妈还严。只要我不听话,她就会不高兴,甚至一连好几天都不理我。”
“她打过你吗?”
“那倒没有。可她不理我的时候,我宁愿她打我两下,也比被冷落强。”
我问:“你们小时候,要是你姐姐抢了你心爱的东西,你会怎么办?”
她不假思索:“当然抢回来!不过通常不用我抢,她自己就会让给我。”
我沉默片刻,在她背上轻轻拍了拍:“不早了,睡吧。”
她依言点头,带着一种踏实的心安,很快便沉入了梦乡。
听着她轻缓而规律的呼吸声,我却思绪翻涌,睡意全无。就这样在纷乱的思绪中,我迎来了天边泛白,等到了窗外城市渐渐苏醒的喧嚣……
我的头痛加剧,恶心反胃,全身肌肉酸痛,还伴随着低烧……
医生检查后,给出了诊断意见:病人因用脑过度引发过度疲劳综合征,同时软组织损伤导致了炎症反应。
他明确要求彭晓敏:“从现在起,暂停探视,减少病人与外界的交流,尤其要避免情绪波动,必须保证充足的营养和睡眠。”
彭晓敏将这些医嘱奉为圣旨,开始切断我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连手机也被收走了。
我开始陷入昏沉,意识模糊,昼夜颠倒……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意识终于挣脱混沌,渐渐清晰。睁开眼,彭晓敏正用手擎着下颌,忧心忡忡地俯在床边凝视着我。
见我苏醒,她脸上立刻绽开欣喜的笑容:“你醒了!感觉好点了吗?”
我点点头:“轻松多了……现在几点了?”
她瞥了眼手机:“上午八点多了。”
我用舌头舔了舔干涩的嘴唇:“给我换衣服。”
她一愣:“干什么?”
我语气不容置疑:“我要去送前进。”
她惊讶地睁大眼睛:“你怎么知道是今天?”
我撑起身,一阵眩晕袭来:“胡嘉和你说话……我都听见了。”
“你不是一首昏睡吗?都听见了……”她有些难以置信。
“别问了,”我打断她,“把那套衣服拿来。你也去换,你来开车……还来得及。”
看我神色坚决,不像玩笑,她不再多言,立刻转身照办。
从医院到县殡仪馆的路,耗了一个多小时。小敏车开得慢,我也不敢催促。
赶到时,离十点还有些时间。她扶着我走进休息室。刚一进门,我的目光就钉在了一个戴孝的中年妇女身上她身边还跟着两个同样披麻戴孝的男孩。
这一定是项前进的嫂子了。我甩开小敏搀扶的手,强忍周身不适,一步步挪到嫂子面前。
她是个被风霜刻蚀的农村女人。丈夫死于事故,好不容易盼到小叔子有了份体面工作,能撑起这个家,如今这根顶梁柱也轰然倒塌,撇下了孤儿寡母。生活的重担早己压弯了她的脊梁,眼神里是洗不尽的疲惫与哀伤。
她虽没见过大世面,却有着最本真的朴实。见我走近,从我衣着上大致猜出领导身份,下意识地伸出手想握。
我哪敢去碰那只手?一股沉重的愧疚压得我抬不起头,只能在她身前深深弯下腰去这一躬,是我能献上的最卑微也最沉痛的歉意。为了救我这条命,她又永远地失去了一位至亲。
我的举动让她吃了一惊。她慌忙上前,双手托住我弯下的脊背,不住地说:“使不得,使不得啊……”
我猛地抓住她那双粗糙的手,泪水再也无法遏制,哽在喉头的声音发着颤音:“嫂子……我是关宏军。”
她瞬间僵住了。眼睛瞪得极大,嘴唇哆嗦着张了张,却发不出半点声音。只有那双被我紧攥的手,像风中落叶般剧烈地抖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