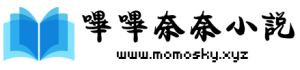“如果是陈小伟让你们来的,那就让他自己滚过来跟我说!”
话音未落,她脸色骤然转冷,手腕一甩就要把厚重的实木门关上。.d+a.s!ua?n·w/a/n!g+.\n`e_t¨
我抬手,用手掌抵住了门板,沉稳的力道让门纹丝不动。
“朱小姐,我们不是陈小伟派来的。”
门上的铭牌刻着一个古朴的“朱”字,我便如此称呼她。
她透过门缝,一双眼睛重新审视着我,目光里满是戒备与怀疑。
“不认识你们,你们找我做什么?”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盛楠。”我开门见山,“陈小伟请我来,解决他公司公交车的事。但他对我隐瞒了一些关键的东西,我没办法,只能来您这里了解一下。”
或许是“隐瞒”这两个字触动了她心中某根紧绷的弦,她眼中的锐利消散了些许,沉默片刻,终于还是拉开了门。
“进来吧。”
踏入朱家庄园的瞬间,我便感到一股与外界截然不同的气息。
院子极大,足有两三千平,游泳池花园草坪,一切现代豪宅的标配都尽收眼底。
但真正吸引我注意力的,是那些建筑之外的东西。
门口那八棵参天松树,左四右四,看似威武,在我眼中却构筑成了一座凶煞的风水大阵。ez?k/s,w·.?ne^t
八鬼守墓。
这是用在阴宅上的格局,居然被堂而皇之地安在了一座活人居住的阳宅门口!
更让我心头一沉的是,穿过庭院,我又看到了四根散落在不同方位的石柱,样式古旧,布满风霜的痕迹,与整个庄园的现代风格格格不入,却隐隐与门口的八棵松树形成了某种呼应。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风水问题了。
这是在用养鬼困鬼的阴宅法子,来布置一座给活人住的家。
整座庄园,阴气弥漫,宛如一个巨大的冰窖,明明是白日,却透着一股子深入骨髓的寒意。
我们跟着朱小姐走进别墅大厅。
房子内部更是空旷得吓人,挑高的大厅,巨大的水晶吊灯,足以容纳几十人聚会的空间,此刻却只有我们三个活人。
人气,严重不足。
这样的屋子,风水上称之为“宅欺人”,阴气会不断滋生,阳气则会飞速流逝。
长居于此,不病才怪。
朱小姐指了指宽大的沙发:“坐。”
她给我们倒了水,自己却坐到了一张单独的单人沙发上,与我们隔开了一段距离。
她点燃了一支烟,姿态娴熟,显然是个老烟民。¢x¢nsp¢7^4¢8,.c¢o·m/
青白的烟雾从她唇间吐出,模糊了她的表情。
“陈小伟那个人,呵。”
她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轻笑。
“别说你们了,我跟他睡了快二十年,都分不清他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
“既然你是来解决车祸的,想问什么就问吧,我知道的,都会告诉你。”
她的语气很平静,似乎公交车接连出事,也在她的意料之中。
我没有急着去问太岁,反而抛出了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朱小姐,陈小伟是你们家的上门女婿吧?”
一个人能发家,靠自己还是靠祖荫,面相上看得一清二楚。
陈小伟的面相,是典型的“借运”之相,他的富贵,并非源于自身。
“是。”她回答得没有丝毫犹豫,“我们是自由恋爱,他追的我。那时候他从外地来,一穷二白,我爸就一个女儿,没儿子,就招了他当上门女婿。”
“所以,他现在的一切,都是您父亲留下的?”我追问。
“是。”
朱小姐又吐出一口烟圈,眼神飘向窗外空旷的庭院。
“没有我爸,他陈小伟什么都不是。”
“我爸在世的时候,他比谁都乖,我爸让他往东,他绝不往西,把我爸哄得开开心心,最后把所有家业所有人脉,都放心地交到了他手上。”
“我爸前脚刚走,他后脚就露出了真面目。”
她语气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冰冷。
“他倒是不敢打我,但他可以几个月不回这个家。这种冷暴力,比挨一顿打,要残忍多了。”
果然如此。
陈小伟在我们面前吹嘘自己如何白手起家,一步步打拼到今天,对自己是上门女婿,继承岳父家产的事,却是只字不提。
这份城府,这份心机,确实可怕。
突然,朱小姐的目光转回我们身上,直勾勾地看着我。
“他在外面养女人的事,你们也知道了吧?”
吴胖子忍不住插话:“知道,就是他那个秘书!朱小姐,他就是个上门女婿,还敢这么对你,你怎么不一脚把他踹了?让他净身出户!”
朱小姐闻言,只是淡淡地看了吴胖子一眼,那眼神仿佛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她没有回答,只是又抽了一口烟。
烟雾缭绕中,她的声音带着一丝自嘲。
“我们是自由恋爱,我爱过他,这是真的。”
“而且,我生不了孩子,结婚这么多年,是我对不起他在先。他在外面找人,如果只是为了要个后代,我认了。”
“什么?”吴胖子下巴都快惊掉了,“他对你这样,你还觉得是自己对不起他?”
朱小姐笑了,那笑声里充满了无奈和苍凉。
“不然呢?离了婚,我再找一个,哪怕找十个,哪个不是图我家的钱?”
“我这把年纪了,你觉得我还能碰见所谓的真爱吗?”
“谁对我好,谁对我假,我心里跟明镜似的。陈小伟现在是对我不好,可他至少,真心对我好过。”
“人这一辈子,短短几十年,能遇到几个真心待你的人?”
她的话,让整个大厅都陷入了沉默。
这是一种绝望后的清醒,一种看透人心的悲凉。
我等她情绪平复了一些,才继续问道:“朱小姐,那您了解陈小伟的过去吗?在认识您之前,他是做什么的?”
朱小姐的思绪似乎被拉回了很久以前。
“他父亲以前也是做生意的,后来破产,自杀了。”
“他十五岁就出来闯社会,去过很多地方,吃过数不清的苦。”
“二十五岁那年,他流落到中海市,开了个小服装店。我就是去买衣服的时候认识他的。”
她的眼神里,难得地流露出一丝温柔的怀念。
“那时候的他,风趣体贴,对我无微不至。说真的,除了我爷爷和我爸,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对我那么好过。”